


柳立子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所所长
罗飞宁
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青年探索》编辑部副编审
摘要:本研究以广州近代西餐业为研究对象,将餐饮空间置于城市近代化转型的复合语境中,系统考察西餐业这一新型业态与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社会交往模式及日常生活方式的互动关系。通过历史文献分析与跨学科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揭示出西餐业不仅作为商业实体,更作为承载文化碰撞、阶层重构和现代性体验的多维社会空间,其发展轨迹映射出广州从传统商埠向近代都市转型的深层机制。研究发现,作为广州商贸网络建构与服务经济勃兴的衍生品,西餐业既重构了广州餐饮的区域版图,又延续粤菜饮食风味而创造出“广式西食”,通过物质消费与符号消费的双重机制,催生出具有现代特征的餐饮文化与市民文化。
关键词:广州;近代西餐业;城市空间;城市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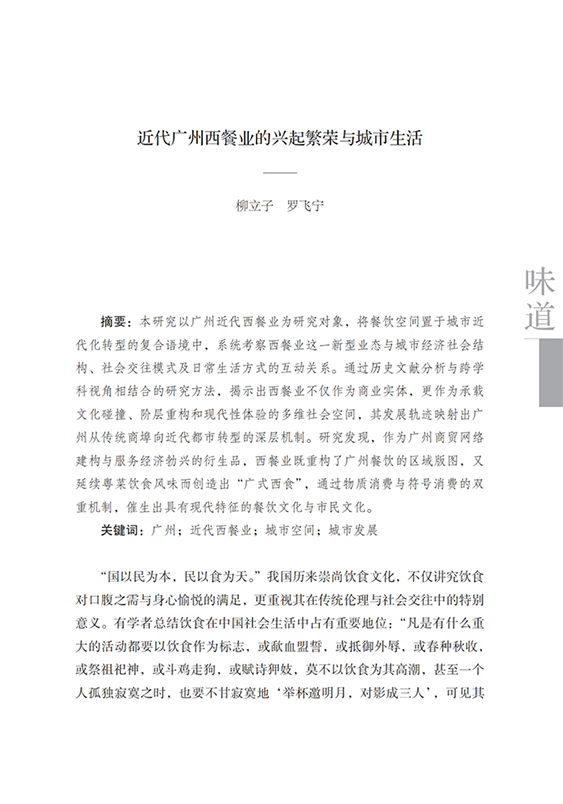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国历来崇尚饮食文化,不仅讲究饮食对口腹之需与身心愉悦的满足,更重视其在传统伦理与社会交往中的特别意义。有学者总结饮食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凡是有什么重大的活动都要以饮食作为标志,或歃血盟誓,或抵御外辱,或春种秋收,或祭祖祀神,或斗鸡走狗,或赋诗狎妓,莫不以饮食为其高潮,甚至一个人孤独寂寞之时,也要不甘寂寞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可见其涵盖面的广泛。”[1]因此,通过饮食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对城市也同样,餐饮业不仅反映这个城市的饮食特点,更可以从中解析饮食与城市经济发展、社会演变、生活风尚的关系,从而呈现城市的发展轨迹和形象面貌。
广州自古就是我国南方重镇,濒临南海,河涌纵横,雨量丰沛,果蔬众多,禽兽生猛,鱼虾无数,是中国饮食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唐代广州的“南味”“南烹”已经以其独特而闻名全国;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商业性农业走在全国前列,广州市场兴旺,对内对外贸易发达,城镇周围又分布着许多圩市,群众生活比较富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珍馐佳肴。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广州餐饮行业也得到长足发展。清末,随着进入我国的西方人越来越多,西餐烹饪技术也逐渐传入,1860年广州出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西餐馆—太平馆,它标志着西餐业正式在广州乃至中国开始生根,也标志着西式食物、食具、礼仪逐渐被国人接受,中国传统的饮食习俗逐渐发生转变。
一、通商往来,西餐由广州率先登陆
西式餐饮的传入,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前期。目前能查阅到的相关记载是英国人威廉·希基1769年8月在珠江畔的英国商馆的见闻:“人们一般会在自己的房间里用早饭,下午两点到五点,大家齐聚大厅,共进午餐。午餐是一场盛会,菜式丰富,还有红葡萄酒、马德拉白葡萄酒、蹄膀肉。下午七点左右,大厅还会提供茶水喝咖啡。东印度公司的成员们,几乎把伦敦西区上流社会的绅士生活场景搬到了珠江畔的英国商馆内。”[2]很显然,西餐是随着广州与外国通商的不断交往逐步进入中国的,最早出现在广州的外国商馆和外商家中,一些华仆已经能做很丰盛的西餐,还能配合上很繁复的西式餐具和款待礼仪。
几乎同时,为了与外商建立并保持良好的交往互动,宴请聚餐无疑是最好的拉近距离、相互认识的机会,因此与海外联系较多的商人群体已经深度接触西餐。据程美宝、刘志伟教授考证:“中国行商家庭的厨子,很早就懂得炮制西菜,因为行商经常要招待洋商和外国使节。早在1769年,行商潘启官招呼外国客人时,便完全可以用英式菜式和礼仪款客。”[3]作为“十三行”同文行的创始人,潘启官做洋行生意以前,曾三度南下菲律宾做生意,粗通外语,也了解国际贸易中的基本礼仪。创办洋行后,他常为外国商人与船长举办宴会。宴会往往分两场,一为西式宴席,潘启官为在场的每位中外宾客准备刀叉,晚上有中国戏剧助兴;二为中式宴请,大家都用筷子,晚上宾客们在主人家的花园里欣赏烟火、杂耍和魔术表演。[4]因生意需要,广州大部分行商都像潘启官一样,熟知西方基本礼节,与外国商人关系良好。中和行的老板潘文涛,学会了打西式纸牌,在洋人圈里成了名人。[5]曾任广州英国商馆总负责人的J. T. Elphinstone,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一位叫潘有度的中国人,赞扬他精明能干,比起和他做生意,自己更喜欢和他一起吃饭。[6]
然而由于清政府实行垄断贸易,西餐较长时间内也只为十三行商人和极少数开明的广州当地高级官员所熟悉和认同,并进而成为他们认知与理解西方文化的重要窗口。如道光年间的广州文人马光启曾经详细地介绍“番鬼大餐”:“桌长一丈有余,以白花布覆之。羊豕等物全是烧熇,火腿前一日用水浸好,用火煎干,味颇鲜美。饭用鲜鸡杂熟米中煮,汁颇佳,点心凡四五种,皆极松脆。”[7]这样的记述很显然说明其有过不止一次的品尝和经历,颇有常客之风范。京官李钧,则于道光八年(1828)巡视广州时对洋人习俗充满好奇,他在日记中写道:“广州府请饭后,登鬼子楼……凭栏一眺,极目青苍……饮鬼子酒数杯,五色味甘。楼上无一夷人,盖有司先期遣也。”[8]未见着洋人,也没吃西餐,却对洋人酿造的酒欣赏有加,对商馆建筑的精致也颇为赞叹。即便是徐珂这样担任《外交报》编辑多年、见多识广的人,对于西餐入华的认识也并不够全面,他在《清稗类钞》中有记:“国人食西式之饭,曰西餐,一曰大餐,一曰番菜,一曰大菜,席具刀、叉、瓢三事,不设箸。光绪朝,都会商埠已有之。至宣统时尤为盛行。”[9]这显然严重忽视了西餐在广州的登陆和流行都要早于其他城市的事实。
二、下沉民间,短时间成为消费新宠
广州乃至中国的第一家西餐店太平馆初创于1860年,创始人为徐老高,因为地点设在太平沙而得名。徐老高出生时正值鸦片战争,那时广州的沙面岛洋行林立,他就在其中的一家洋行做厨工。外国老板比较严苛,稍不顺心就开口责备。徐老高性格耿直,终于因为顶撞被逐,转做小贩。他挑起担子,做起牛扒生意,随街叫卖。因为价钱便宜,一两毫也可以品尝,所以广州人在街头也可以吃得起“西餐”。他的手艺好,医生、学者以至官员都争相购买,后发展成为著名的西餐店。[10]在咸丰年间与徐老高有类似经历的一些人,曾经在外国商馆做过厨师,通过在广州街头沿街叫卖煎牛扒积累了一定资本后,开起了海记、高记、一趣楼、东园等一批个体小店。这些餐馆对西餐的经营有一定的考究,对偏爱西餐的人士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是由于餐馆一般只经营牛奶、奶茶、多士面包和少量的肉食,品种不太多,高级西餐的消费较为少见,如果顾客要享用较多品种的西餐,必须预订。[11]这些小餐馆对西式饮食方式在广州市民大众间的流行和消费者的培育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像太平馆这样的著名老字号,所经营的传统名牌西菜,如红烧乳鸽、德国咸猪手等招牌菜,到现今已经演变成为广州中西餐厅都能吃到的广式名菜。
随后,广州许多的中餐酒楼纷纷调整经营方式,将酒楼改造为中西餐结合或者专营西餐,推出西餐品种,以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西餐的价格,到了清末,也不是很贵,如岭南酒楼就在报纸上大做宣传:“烹调各西菜,美味无双,并巧制西饼,一切便来往小酌。西餐价格:全餐收银五毫,大餐收银壹元。”[12]甚至澳门的一些经营西餐的酒楼也经常在广州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如澳门日照酒楼在《广州白话报》上的广告:“大小西餐,脍炙人口,中西人士,均赞不谬。”[13]澳门天香酒楼的西餐广告更有意思,称“人情厌旧,世界维新,铺陈可尚洋装,饮食亦与西式,盖由唐餐具食惯,异味想尝,西餐盛行”[14],这或许可看成时人对西餐消费动机进行的分析。至于为何澳门酒店要在广州报纸上登广告,实际上是因为1757年乾隆上谕番商贸易只限在广州一口进行,后又颁布多项约束驻广州外商的规条,包括“外人到粤,令寓居行商馆内,并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外商不得在省住冬,须前往澳门居住等例”。[15]这进一步佐证在一口通商政策的实施下,已形成了澳门和广州两个西方人的聚居区,当时这些颇具规模的西餐店瞄准的消费人群正是在广州与澳门之间经常往返的官商富绅。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餐越来越成为上层社会流行的社交手段,西餐菜品也越来越成为高级酒店吸引高端消费者的菜品标志。19世纪末,广州西餐已发展到足以接待最高级别的外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891年4月初,俄国尼古拉二世一行乘船经香港来到广州。为了迎接俄国王储,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不仅特地到码头迎接,还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席来招待俄国王室一行人。“皇室旅行者伴着‘亚速号’乐队的音乐声在两广总督一个专门的幔帐里(对着花园)用餐”,不仅准备了丰盛的“本地佳肴”,还有一半菜肴是按照欧洲口味做的;“除了刀、叉、勺,也给我们摆了象牙筷子”。不过,俄国人似乎对广州菜肴更感兴趣,评论道:“富有的中国人天生是世界上最讲究的美食家和最殷勤的主人。……富裕人家餐桌上的水果来自波斯湾、巽他群岛、印度和暹罗。”[16]
三、集中经营,两个地段成行成市
西餐毕竟是外来饮食,在原材料、调味佐料和饮品等方面都有特别的讲究,采购渠道和成本均与中餐有明显差别,对主厨及辅助团队也有较高要求,这些都要求有较大投资才能支撑,所以客源指向性较为明显。因此,开店地点的选择,对生存和发展特别重要。太平馆的车水马龙给西餐馆选址提供了最好启示,就是地段必须旺中带洋。太平馆地处南关闹市,靠近天字码头,常有外轮停泊,为洋人必经之路;民国以后,这里又先后出现了海军同学会、国民花园舞厅、海员俱乐部等充斥大量高端客源的机构和场所。
民国以后,西风东渐日盛,广州已有不少教堂以及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由洋人控制的洋行、银行、邮政局、粤海关等机构也多了起来,而且华侨也大举投资广州的各项事业,这些机构的工资福利远较国内水平高,形成一个消费能力较强的阶层。受新的社会风潮影响,军政界、企业界的人员也喜欢以西式宴会来应酬。到了20世纪30年代陈济棠主政时,百业兴隆,外贸繁荣,加之受港澳影响,西式活动如舞会、晚会、西式婚礼、教会节日、欧美同学会等成为一种时髦,很快广州西餐馆增加到30多家。投资西餐业的,有本地资本、华侨资本,还有一些外国的资本。到了民国后期,则以华侨投资最多。
20年代前后,新开办的西餐馆大中户大多集中在两个地方。一是城内商业繁盛区—永汉路、惠爱路(即北京路、中山路)一带,这里有不少军政机构。这些西餐馆的营业对象主要是省市军政界官员、知识界人士、留洋同学会成员。在这一地段,出现了十多家西餐馆,其中以太平新馆和哥仑布生意最好。二是地处珠江河畔的沙面内外,这里历来就是华洋杂处地带,与之连接的西堤、长堤大马路一带,有粤海关、邮政局大型百货公司、旅行社、戏院、游乐场、银行等,而且还是鳞次栉比的客轮码头集中地。在长堤一带,就云集了东亚酒店餐厅、华盛顿餐厅、爱群酒店餐厅等名店,主要以企业界、钱庄界以及华侨、旅客、流动商贾、交际花等为经营对象,有时也有高官巨贾;在沙面岛上,则出现了经济、域多利、莫斯科等店铺,顾客以洋人为主(多光顾经济餐馆)。此外,也有一些小的西餐馆开设在侨眷区(东山)、教友区(医院、教会附近),以及旅游区(荔枝湾)的,当然也有在闹区经营的。[17]
四、环境讲究,始终引领消费时尚
20世纪20年代以后,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西餐馆,像在广州城刮起了一股清新的饮食旋风,让市民耳目一新,不论装潢陈设还是环境打造,都与我国传统的餐饮业有着明显的区别。
西餐馆一般不再设在矮楼木屋之内,而多是设在高楼大厦之中。即使在由旧馆发展过来的平房旧屋,也要加以修建改造,增添陈设,力求华丽。餐室内灯光柔和悦意,环境幽雅,桌椅都换上时兴的低矮型克罗米桌椅,舒适整洁。如大公餐馆就采用高背式沙发椅,并率先装上冷气;英华特意从香港引进新式电镀钢枝软垫折椅;哥仑布餐厅上三四楼用电梯;温拿餐店辟有小型舞池,用餐之余还可跳舞;亚洲酒店餐馆和日日新餐馆设有桌球室供食客消遣。总之,西餐馆与酒楼、茶楼的热闹喧嚣形成强烈的反差,以清静舒适为特点,来上馆光顾的客人彼此说话都很小声,一般不存在“搭台”的情况,故除一同到来的客人之外,不同桌的客人相互听不清楚说话声。为了适应顾客的需要,不少馆厅还播放一些抒情的轻音乐,客人也可点唱,尽量使人能在宁静的气氛中感到宽慰和舒适。餐馆的外观,则都有鲜明的西食标志,挂出醒目的招牌,有些大店还配上红绿霓虹光管引人注目。
西餐馆在服务方面也更为周到细致。规模稍大的西餐馆,门前都有男性侍者等候,负责开汽车门或引领客人进餐室。在服务程序上,尊重西方习惯—女宾在先,男客在后,如有儿童小客,要另行设高椅。按规定,客人先到先坐,后来者不能搭台,万一需要,服务员可主动代为征询,答复肯定后方可。客人落座后,服务员会奉上冰的苏打水或红茶,然后轻声细问客人的口味,态度恭谨。为了保持餐室清静,服务员就算与熟客接触都是“阴声细气”的,职工绝不能相聚谈笑。包房客人不按铃,服务员不可随便进入。菜式随点随烹,上席次序有条不紊。为了方便顾客,各种名酒都可以原支或按杯供应。餐具摆设和使用,也严格按照西食的要求:面包碟放在客人的左前方,上置面包刀一把;各类酒杯和水杯则放在右前方;中间放餐巾,叉放在餐巾之左,汤匙和餐刀则放在餐巾之右。客人吃完一道菜时,便将叉、刀合拢并排放在餐碟中央,这是叫服务人员将碟及叉、匙、刀拿去的信号。如果客人在进食中途停顿,把叉、刀左右分架在碟上,则表示他还没有吃完,只是食中的“小休”,服务人员则不能把它拿走。
餐馆餐厅的卫生要求是比较高的,要求窗明几净,厕所保持清洁。端饮食与搞清洁的人员是两套人马,各自均有明确分工,互不代替,食品由前者担负,卫生是后者的职责。客人在食用中弄坏碗碟,及时更换,立即清理;偶尔丢下杂物在地,迅速清扫,哪怕只是丢了一支火柴头尾亦是如此。每一位工作人员,衣冠是否整洁,发型是否恰当,指甲是否剪平,都由部长、班长检查之后才准上班的。
五、全天营业,主要盈利靠承办酒会
西餐馆厅主营西餐,兼营西饼面包冷热饮品烟酒等,每天从早上7时开始至深夜12时不间断营业,一天供应五餐。早餐供应咖啡、牛奶、奶茶、果汁、烩果、奄列蛋、烚蛋、煎蛋、波蛋、粉卷、牛奶粥、通心粉、麦片西米等;午餐11时开始,以供应肉菜和汤类为主,奶茶、咖啡和牛油面包是常备品,前两种必须叫点,后者在开餐前照例先行送到,吃用与否,任随客意,但这时的顾客进食不会很多,通常是一汤一肉;茶餐在午后4时开始,只供应奶茶、咖啡、西饼、三明治一类的茶点;正餐下午6时30分至9时,习惯进食西食的人每天要有一顿肉类较为丰富的餐次,称为“正餐”,故这个时间是西餐馆人气最旺的,每当华灯初上,多种形式的酒会、宴会便拉开序幕;夜宵时间是晚上10时至12时,顾客人数比早餐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般爱吃冷熟肉配沙律,至多增加一个汤,接着便是咖啡或奶茶了。
当时经营西餐,赚钱主要是靠酒会和宴会,如鸡尾酒会、冷肉酒会、圣诞节狂欢宴以及婚礼、生日茶会或宴会等。鸡尾酒会是一种隆重的应酬酒会,以酒为主,不设菜式和餐具,只备花生、果仁、咸点心、炸薯片之类干性食品,以便流动祝酒、互相交谈时随手吃用。冷肉酒会,其性质和形式与鸡尾酒会基本相同,只加添几盘冷熟肉而已。圣诞节是西洋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宴会通常于每年12月25日前后一周内举办,是西餐行业一年中生意最为兴旺的时候,也是各西餐馆最赚钱的时候。这些酒会和宴会,订客多是军政界和洋行大企业界,与会人数从二三十人至百余人不等,办一次就会赚很多钱。为了争夺这些高等顾客,名店都很注意结交政界人物,拉拢熟客,尤其是经办筵席的科室人员,不但在年节期间定期送礼,而且还经常请相关的办事人员吃饭,并开展长期交际活动。太平馆之所以能长期居于广州西餐龙头地位,与其营业对象以军政界为主、能长期拉到宴会订单有极大关系,当时蒋介石、林森、李宗仁、宋子文就时来光顾,陈济棠更是常客。
六、注重管理,精心烹制“广式西食”
由于竞争激烈,西餐馆常重金聘请熟练的管理人才,不少店铺都是请司理来管理的。司理的收入高于总管一倍左右;总管高于部长一倍左右;部长高于班长一倍左右;班长高于一般服务员一倍左右。也就是说,司理的收入是一般服务员的16倍。20世纪20年代后期,太平南路的新亚酒店曾以优厚待遇聘请原亚洲酒店负责人钟标为司理,后钟标又受聘兼职于哥仑布餐厅,两店都有较大发展,业务兴旺。各家餐馆的司理,对经营都有自己的一套。例如大公餐馆的司理冯佳,他的一贯做法是亲力亲为—亲自选购主要原材物料,时刻注意菜式质量,并早晚检查清洁卫生(特别是厕所);若因公外出,常有电话回来作指示,顺便通过电话,检听播放中的轻音乐曲调是否适当;晚市收歇后,利用夜宵的短暂时间,亲自主持一次碰头会,与总管、部长研究当天营业情况,分析滞旺原因,作出进一步的部署。他搞活门市的策略是:营业兴旺时,多供高档菜式,争取较高利润;反之,则以低档品种为主,转向薄利多销。与同业竞争的应策,更是果断迅速:当同地段的温拿餐馆新辟舞池时,冯佳立即研究陈设改革,因店制宜地装置新型美观的奶黄色壁灯,改设高背沙发,增播名曲抒情唱片,扩大宣传,等等。
同时,西餐馆老板们都意识到,外来的西餐要吸引嘴刁的广州人,必定要精制出质量上乘的菜式,特别是自己的招牌菜。因此,各馆都在此倾注了十二分功夫,都创制出自己叫得响的名菜,这是西餐能在广州兴旺的根本原因之一。首先,各餐馆不惜重金聘请高级西厨,主理的厨师,薪金和店面的司理相近。名馆的高级西厨,如太平馆的张炎、王澄,大公的郑谦、徐金松,经济的周贤等,都是驰誉省港澳的高手,所有名菜佳肴均是他们的杰作。其次,讲究用上等的食材,烹饪制作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以太平馆饮誉数十年的烧乳鸽为例,原料是肥嫩的石岐良种,并派专人用嘴含豆于唇边逐粒向鸽诱食,使之短期内肥壮[18],然后配以优质调料烹制而成。英华餐馆的牛扒及大公餐厅的牛柳,都是以闻名世界的澳大利亚牛为原料。经济餐馆的咖喱鸡选用的是省内首屈一指的清远良种。至于其他各种调味料、香料也大多从国外进口。冷热饮品的原材料,大都是进口货。烹制技术也颇有讲究。华盛顿的咖啡,是自行加工炒制的,香味浓厚;太平馆的咖啡也很出名,除用料好外,烹制时对火候的掌握也非常精准,因为火候过了失味,不足则不出味。
当时广州的西餐,口味上自成一格,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19]西餐有不同派别,东欧味重肥腻,西欧和美国口味清淡。当时广州西菜以英式为依据,并吸收粤菜特点作改良,创制出许多经典菜品,如太平馆的烧乳鸽、焗蟹盖、葡国鸡一直名闻遐迩;华盛顿餐厅则以洋葱猪扒、烧牛扒、焗猪扒饭驰名;新亚餐厅的拿手好菜是焗制品,如焗猪扒饭、焗海鲜饭、焗鸡饭等等;英华餐馆、爱群酒店餐厅、东亚餐厅的洋葱牛扒远近闻名;经济餐馆的咖喱鸡和大公餐馆的焗酿龙虾、荷兰牛柳也很受食客的赞赏;名不虚传的还有哥仑布餐厅、亚洲餐厅、新亚餐厅的西洋焗肾翼、烟仓鱼、牛尾汤、铁扒子鸡等。[20]
从葡萄牙人1514年首先叩关、1577年租占澳门,接着是西班牙、荷兰、丹麦和英国用武力强行输入西方商品,以广州为核心的岭南地区在不断反复的“禁海”“取消海禁”政策更迭中展开与西方文化的互触交流。直到1757年乾隆帝开启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广州一口通商”,广州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港和全国主要的商品集散地,逐步出现了以专业化、商品化为目标的手工业生产体系和商品经济萌芽,西方商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从这里不间断传入。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直接渗入,大批华侨络绎回国开办工厂、百货公司、银行、路桥交通公司、酒家等。从1907年广州的第一家百货公司光商公司开业,每隔三年就有一家更大的百货公司开业,到1916年广州已拥有光商、真光、先施和大新“四大百货公司”。1930年广州城区有店铺2956间,1933年以商业为生的人口有10万人以上,[21]形成第十甫、长堤、惠爱路(今中山五路)三大商业中心。[22]为数众多的商业街成行成市:大同路、东堤的大米业,一德路的京果海味业,濠畔街的皮革制品业,泰康路的山货藤器业,文明路的杂货家具业,大新街的象牙业,文德路的旧书古董业,西来初地的酸枝家具业,仁济西的南北药材业,杨巷的丝绸业,高第街的鞋帽业,上九路的土布业,长堤的洋酒业,北京路的新书业,长寿路的玉器业,等等。[23]
西餐的传入、兴起和繁荣,是广州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城市生活变迁的一个具体表征,反映的却是广州在“西食东渐”过程中对近代中国饮食习俗变革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广州这一时期集中涌现的西餐馆,无论是在建筑、经营方面,还是在器具、陈设方面,一边模仿洋式,一边创出广式,恰是广州人群在面对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之时的智慧融合与转化输出,也是岭南文化得以在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潮流的涌现中勇敢地接受挑战,将之吸收并融糅在自身兼收并蓄的多元文化格局中而获得质变飞跃的明证。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发展出数量繁多、经营细分、管理专业、出品上乘等特点鲜明的餐饮业,使广州成为近代中国饮食行业的引领者,故民谚已有“生在苏州,住在杭州,食在广州,死在柳州”的说法。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广式生活孕育的广州人群,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过程中表现出的中和通达气韵与融合创新能力,正是他们带领着东南一隅的岭南文化走向了全国前列,步入先进地域文化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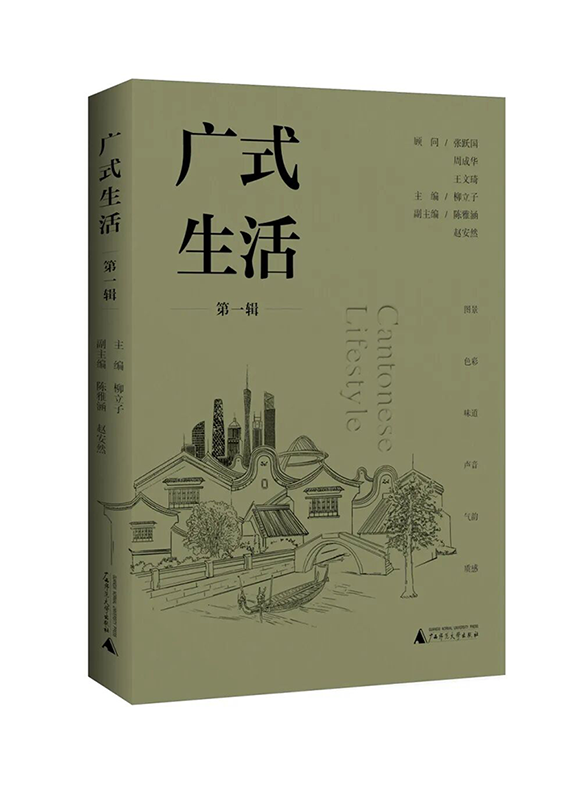
柳立子,广州市社科院城市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
罗飞宁,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青年探索》编辑部副编审
参考文献
[1] 林少雄编著:《口腹之道—中国饮食文化》,沈阳出版社,1997年,第31—32页。
[2][英]孔佩特:《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于毅颖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5—37页。
[3] 程美宝、刘志伟:《18、19世纪广州洋人家庭里的中国佣人》,载《史林》2004年第4期。
[4] 转引自王诗客:《新滋味:西食东渐与翻译》,经济日报出版社,2020年,第108页。
[5] [美]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5—36页。
[6] 转引自王诗客:《新滋味:西食东渐与翻译》,经济日报出版社,2020年,第108页。
[7] (清)关涵等:《岭南随笔(外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3页。
[8] (清)李钧:《使粤日记》,道光甲午年(1834)刻本,道光八年九月二十日条。
[9]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 6270页。
[10] 王诗客:《新滋味:西食东渐与翻译》,经济日报出版社,2020年,第114页。
[11] 蒋建国:《广州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1800—1911)》,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0页。
[12]“岭南第一楼改良食品广告”,载《游艺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八日。
[13]“澳门日照酒楼广告”,载《广东白话报》1907年第2辑。
[14] “澳门天香酒楼广告”,载《广东白话报》1907年第7辑。
[15]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页。
[16] 伍宇星编译:《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32页。
[17] 参见杨志慎等:《广州西餐业发展史话》,载陈基、叶钦、王文全主编:《食在广州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7—211页。
[18] 参见黄曦晖:《太平馆的沧桑》,载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9—220页。
[19] 参见杨志慎等:《广州西餐业发展史话》,载陈基、叶钦、王文全主编:《食在广州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7—211页。
[20] 参见冯佳忆述,黄曦晖执笔:《我所知道的广州市西餐业》,载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7—208页。
[21] 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3页。
[22] 龚伯洪:《商都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
[23] 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3—304页。